
1990年代至新千年的十余年,是中國電影體制改革的轉型過渡期。這一改革轉型起始于1980年代后期中國電影的票房危機,并在1993年之后加速深化。
在整個國家的經濟制度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的變革中,電影的生產體制也從過去的國家統購包銷轉向制片廠自負盈虧。

這種體制的變革,改變了過去相對均等的資源分配方式,使之向那些更有票房潛力的創作傾斜。在更強調效率和利潤的制片環境中,年輕導演、女性導演的生存空間無疑萎縮了。
作為1980年代女性導演群體中的主要成員,第四代、第五代女導演在進入九十年代之后大多難以延續自己帶有女性傾向的電影創作。

或是所拍攝的女性題材電影在“女性意識”上呈現出“落網”或倒退的狀況,其中的很多人(如黃蜀芹、李少紅、胡玫)都轉入了新興的電視劇領域,或是接拍一些中小成本的商業片、娛樂片或主旋律電影。
另一個值得一提的是,我們還可以從“第六代”的出生看到電影體制變革的影響。

作為九十年代的電影學院畢業生,第六代失去了直接進入體制的機會,他們不得不自籌資金拍攝自己的電影,不知是否因為這其中的困難與風險,使得這一代以體制反抗者姿態躍入舞臺的導演中不再能看到女性的身影。
整體而言,占據九十年代至新千年中國電影中心地位的,是獲得更大成功的第五代、帶動市場的好萊塢進口大片以及集國家優勢資源推出的主流大片。

而隨著老一輩導演的淡出、中生代的轉向、新生代的空缺,1990年代活躍著的女導演在人數上顯著減少。
可以說,不論是在商業上、藝術上,還是在主流文化體制內的重要性上,“女導演”和“女性電影”都顯得頗為邊緣化。

在電影出品數量方面,始于1993年的電影體制改革的影響在1995年之后逐漸顯現出來,電影產量連年下跌,從九十年代前期的年均近150部下降到年均90余部,其中產量最低的1998年僅出品了82部影片。
這其中,女導演的出品數在總量上與八十年代大致相當,有180余部,從1990年代前期的年均20部以上,下滑至后期的年均十部左右。

與上一個十年情況一樣,這些作品中以女性為中心的影片總體并不占多數,據我粗略統計,十年下來這個數字停留在30部左右,且主要集中出現在九十年代前期,到1995年之后,“女性電影”就幾乎絕跡于國產影片目錄了。
事實上,我們不能把九十年代的女性電影及其批評同八十年代的分隔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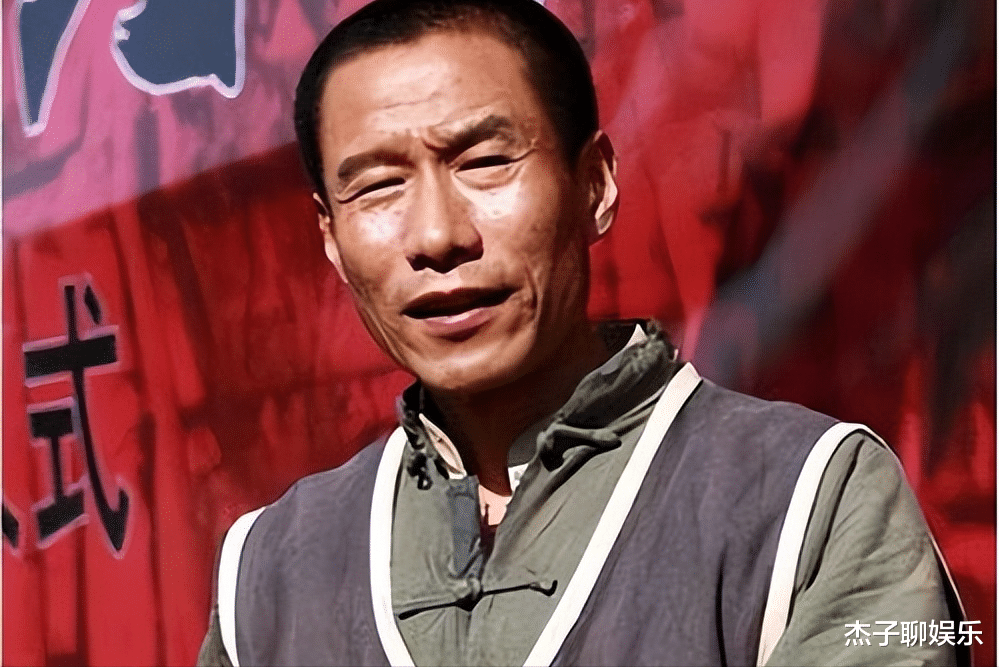
從它的發展歷程來看,1980-1990年代的二十年應當被視為一個完整的從興起到落潮的過程:1980年代前期是女導演創作逐漸興起并引起關注的階段,1980年代中后期至1990年代前期是女導演創作的高峰期,1990年代后期,這一始于八十年代的潮流漸漸退去。

從影片內容的角度看,1990年代的女性題材電影(包括男性導演拍攝的),大致有三種類型,其一是延續八十年代文化反思和文化尋根主題的女性題材電影,這其中,文化反思敘事在九十年代的語境中已失去號召力,其對女性形象的扭曲呈現也導致自身在藝術上的失敗。

文化尋根敘事則由于其對傳統女性道德的推崇而被女性主義學者批為“男權的反攻倒算”。故而這類歷史文化敘事在九十年代逐漸淡出。

其二是展現市場化改革以來不斷出現的新型職業女性,如女經理、女老板、下崗女工、打工妹、外企女白領等形象,這類影片整體上反映了社會變革之后女性所獲得的新位置、新身份,但是在女性主義的標準下,它們是進步還是倒退還值得進一步研究。

其三是以女性為主要角色的商業娛樂片,這類影片通常以諸如舞女、女歌手、女警、女囚犯、女保鏢、女俠等易于引發觀眾獵奇心的角色為賣點。
需要指出的是,這些數目可觀的女性題材影片中,男性導演的創作占據大部,其中較優秀的作品如《香魂女》《二嫫》等也多出自男導演之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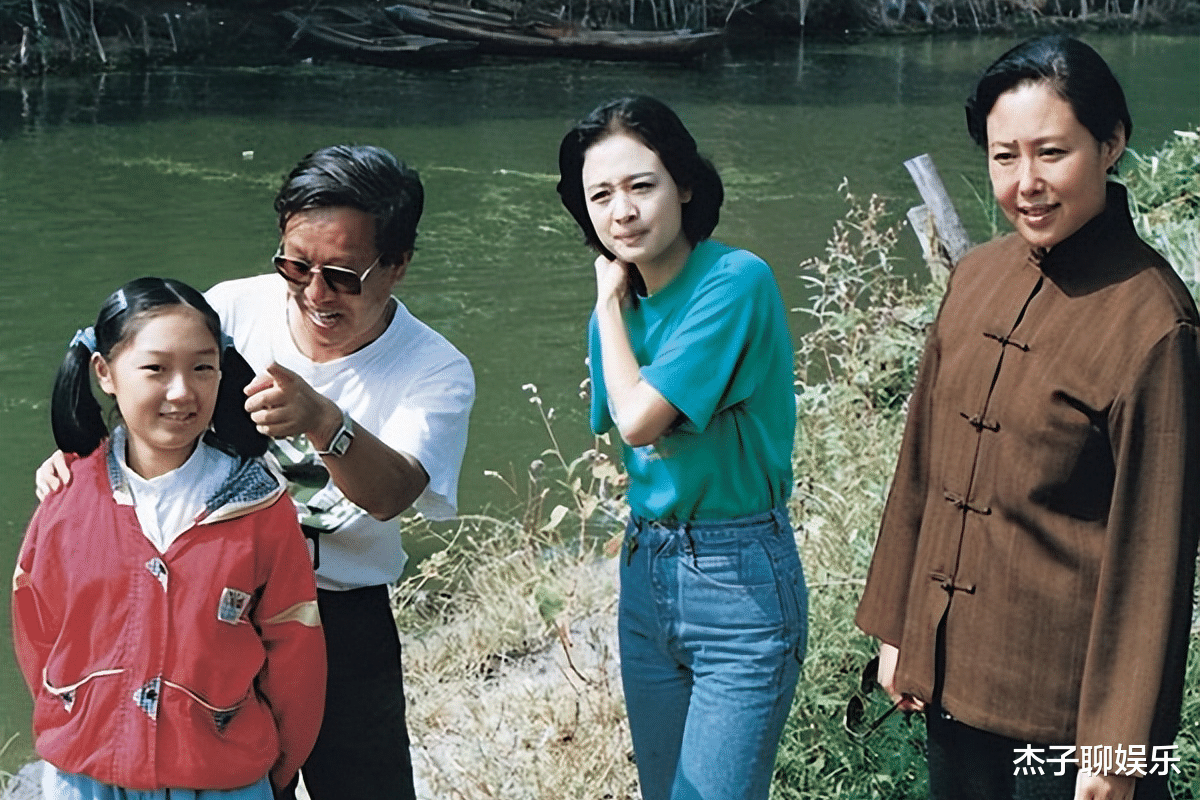
若僅看女導演,在她們數量不多的作品中,我們也依然能夠看到她們對女性主題的關注,如董克娜、黃蜀芹、史蜀君、秦志鈺、李少紅、鮑芝芳以及通過合拍片渠道進入大陸的許鞍華、張艾嘉等女性導演在九十年代的創作依然顯示出清晰的女性傾向。

她們的《女性世界》《奧菲斯小姐》《燃燒的婚紗》《獨身女人》《女人·TAXI·女人》《早春一吻》《夢醒時分》《離婚》《紅粉》《第一誘惑》《畫魂》《半生緣》等都是在體制變革的大環境中完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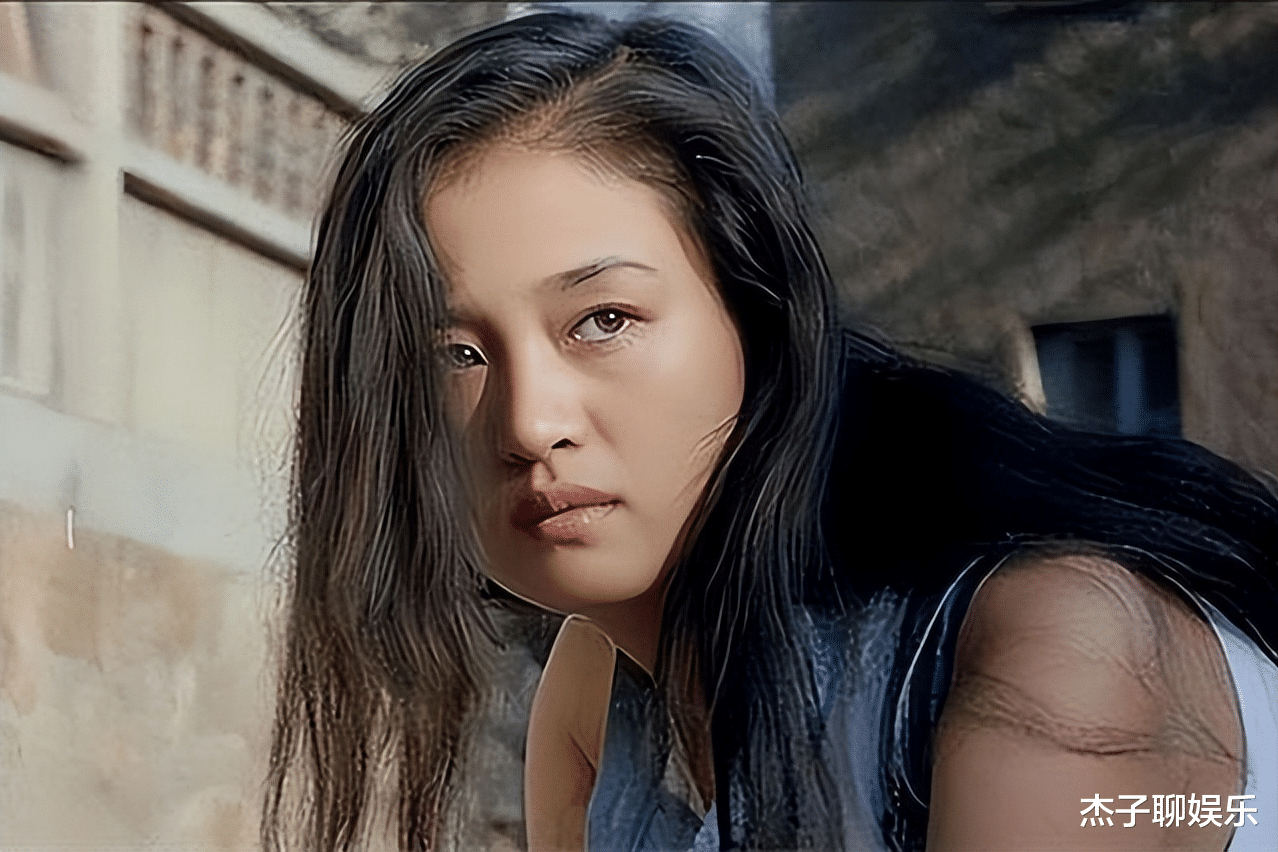
盡管這些作品在美學上未必成熟,在女性表達、女性意識上也未必符合女性主義的期待,然而正是這些作品與女導演們的創作活動本身延續了中國電影中已然非常微弱的“女性電影”聲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