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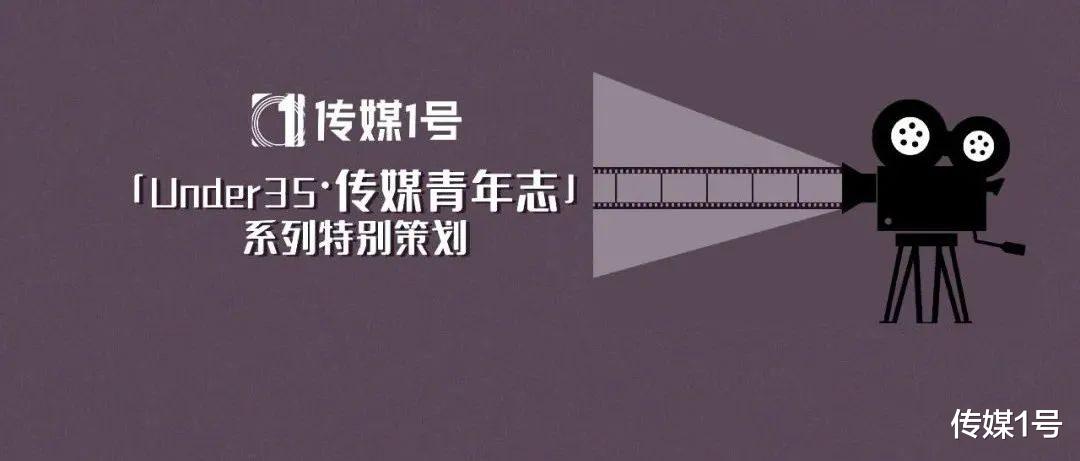
一份青年制片人的成長日志。
任何時候,決定行業發展的,是人。
文娛行業不復昔日風光,相比離開者,堅守者更值得我們尊敬與關注。
因此,本月《傳媒1號》正式推出「Under35·傳媒青年志」系列特別策劃,嘗試將視角聚焦到那些堅守在文娛行業的35歲以下這一年齡層的青年傳媒工作者身上。這群人有著自己獨特的魅力點:
他們是堅守者,但又非常年輕;他們是夢想家,但又腳踏實地。
首期「Under35·傳媒青年志」,我們的目光投向了制片人這一文娛行業內具有中樞性功能的角色,以「Under35·青年制片」為題,以青年制片人光汐和尤丹的從業經歷和生活狀態為主線,嘗試去探討這樣一個話題:什么是成長?
年紀的增長,職位的晉升,作品的積累,還是視野的轉變?
也許對很多人而言,成長的本質是妥協。年少時認為自己無所不能,后來才發覺自己只是個普通人,于是選擇順著人潮走下去,在深夜時偶爾想起自己最初的夢,然后再感嘆一句「人生無常」。
但是對于青年制片人光汐和尤丹而言,成長的本質是執著。在充分認識了制片人這個職業,認識了自己之后,他們依舊選擇成為制片人,依舊想要做出好的作品。
作為青年制片人,他們也許沒有資深制片人那樣深厚的積累,但他們有對于夢想的執著,有一往無前的沖勁,有內容創作的熱情,有重頭再來的勇氣,也有誠以待人的坦率。
推開「世界」的門
「我目前還是想自己闖闖」。
光汐掛掉了某頭部影視公司打來的電話,拒絕了該公司拋出的offer。他快畢業了,憑借著之前的一次創業經歷,以及在該公司積累下來的制片經驗,光汐的第一想法是創業。
隨后,他買了一首歌的版權,打算和其他幾個人一起張羅這個項目的影視開發。從大四下學期一直到臨近畢業的幾個月,光汐全身心地撲在了這個項目上。但事情并非他想象的那么順利,很快這首歌被爆出侵權問題,隨之而來的是整個項目的全部崩盤。
一切都是勢頭滿滿,然后又突然結束。
光汐遇到了他職業生涯的第一個挫折,他不知道該往何處去。項目崩盤后,光汐沒有收入來源,非常苦悶。他說,「那個時候我就基本上是天天打王者,從晚上打到早上五六點,然后出去吃個早餐,吃完回來就睡覺,睡到下午五六點,然后再起床。」
沉淪了將近一個月后,光汐決定出去找工作。他受夠了日漸消沉的自己,只要能找到一份工作,干什么都可以。那個時候光汐的一位師哥找到他,說自己跳槽了,希望光汐過去幫襯一把。光汐連忙答應了,等到真正工作的時候他才發現,這其實是個商務崗位。
他并不喜歡這份工作,他開始認真思考自己的擇業問題,自己想做的到底是什么樣的工作。在這段時間里,他看了很多藝術類的小說,等到實習期快結束的時候,光汐終于下定了決心說,「我還是想做制片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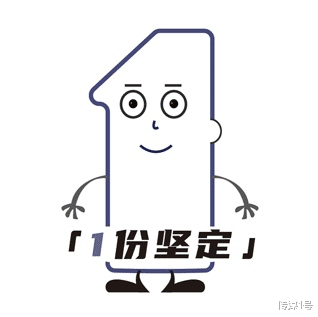
然后他約了他師傅,也就是之前拍劇時帶他的制片人,以及一位美術指導,三個人一起吃了一頓飯。據光汐回憶,當時他覺得自己很失敗,但他師傅卻反問了他一句話說:
「你還愿意回來嗎?你要是回來,在這邊待幾年,把該學的學好,你再出去創業一定能實現你自己的夢想。其實我希望你能實現自己的夢想,因為我已經沒有機會,沒有創業的熱情和機遇了,但我能幫你去做這個事兒。」
然后光汐回去了,開始在制片行業深耕。從真正進入某頭部影視公司工作到離職創業的這段時間里,他整整拍了五部劇。
與光汐不同的是,尤丹并不是一開始就選擇了制片人這個職業。
回到尤丹的學生時代,當初藝考時她最想讀的是導演專業,也許是命運使然,她后來被錄取到了中國傳媒大學播音主持藝術學院,成了一名播音系的學生。由于在校時期成績優異,她還擔任了校電視臺王牌節目《傳媒人》的主持人和制片人,在那片土壤上采訪了不少影視校友。「《奇葩說》的總制片人牟頔師姐來上過我們節目,記得黎志導演2014年宣傳電影處女作也回到了學校的平臺。」尤丹對于影視的好奇心從那時逐漸萌生了。
畢業之后的尤丹收到了多家傳統媒體和電視臺發來的offer。曾經,成為一個新聞人,是她職業理想,她說新聞是一扇窗,讓我們感覺雙腳踏在大地上;電影是一個夢,生活里的儀式感,和那些暫時不能實現的愿望,都可以通過影像來實現。
后來進入電視臺體制內工作的她,選擇了電影記者這樣一份工作,希望可以通過這份職業記錄和報道更多優秀電影創作的過程。FIRST,金馬影展,香港國際電影節,中國電影金雞獎,都有她的撰稿痕跡。香港監制施南生,導演王小帥,演員趙濤,前金馬評委會主席焦雄屏,金馬最佳配樂王希文等電影人,都接受過她的采訪。尤丹表示,在陪伴中國電影市場快速崛起的那些年里,這份經歷讓自己收獲很多。等到后來網劇等新業態興起的2016年,蓄力已久的她,又恰好迎來了自己的轉型之路。

尤丹在FIRST電影展、香港國際影視展「圖源 受訪者」
2017年,尤丹開發制作了她的第一部作品青春劇《蔚藍50米》,該劇在騰訊視頻播出。還獲得了國家廣電總局精品創作工程獎,并被網友贊譽游泳版的《灌籃高手》。可以說,《蔚藍50米》趕上了2016-2017年興起的網絡劇熱潮,又因為作品本身弘揚的是「熱血、青春、夢想」的正能量主題,還登上了2018年國家廣電總局網絡劇發展報告。

后來,尤丹也因此而走上了制片人這條職業道路,對這份工作也有了更深層的思考和敬畏。為了讓自己的認知更加系統化,尤丹后來又考取了北京大學廣播電視藝術學碩士,碩士畢業作品同時擔任了導演和制片人,還獲得了北大學院獎。
回顧自己過去的從業史,尤丹坦言,「每個人兒時都會有她最初的一個理想工作狀態。我小時候就很喜歡看漫畫和言情小說,放暑假就在家看電影和電視劇,高中時《緋聞女孩》我記得我媽給我買過1-4季全套DVD,同學還羨慕不已,跑到我家來借。」
千禧年初,那個躲在家一集又一集看著《流星花園》DVD的小女孩,因為這部劇知道了柴智屏這個名字。她應該沒想到,后來的自己,有一天也可以成為一名制片人吧。
穿越「寒冬」,堅持「跳舞」的人
「成為制片人」的道路并不平坦。
近兩年來,「影視寒冬」一詞被不斷提及。對于觀眾而言,這也許是沒有好劇可看的無聊與失望;對于平臺而言,這也許是廣告大量流失之后面臨的盈利困局;而對于影視行業從業者而言,這也許是市場低迷之下,試錯成本越來越高所帶來的壓力與挑戰。
一方面,外部環境的變化給影視行業帶來了新的挑戰。宏觀經濟、世界格局的變化、疫情等諸多不確定因素的影響使得整個國民情緒處于偏移的狀態。
另一方面,視頻平臺自身在業務層面的探索還處于相對迷茫的狀態,「如何創新」成為困擾各大視頻平臺的首要問題。光汐提到了愛奇藝的「迷霧劇場」,他坦言很佩服愛奇藝,因為最起碼愛奇藝一直在進行創新,即使「迷霧劇場」第二季口碑下滑,他依然認為愛奇藝是個先行者。

愛奇藝迷霧劇場部分劇集「圖源 豆瓣」
不過,關于愛奇藝「迷霧劇場」第二季口碑撲街這個問題,光汐也表達了他的看法:「第一季愛奇藝用的導演都非常年輕,但是第二季他就不敢用了,換句話說,第一步他敢去嘗試的時候,第二步他反而去求穩了」。
作為制片人,光汐和尤丹都很關心影視行業的內容生產問題。在光汐看來,「影視寒冬」歸根到底還是內容問題:「我們到底要產出什么樣的內容,才能讓觀眾覺得我可以為了內容買單」。
但是,制片人這一角色并非無所不能。
與國外「以制片人為中心」的影視內容生產機制相比,國內的影視內容生產基本「以導演為中心」。所以盡管制片人這個角色不可或缺,但不論是在工資收入,還是在知名度上,制片人都很難和導演相提并論。
隨著近兩年來國劇的興起,制片人的知名度有所上升,越來越多的青年制片人開始從幕后走向臺前,被更多的人認識。在這背后,更多的是他們長久以來的堅守。對此,尤丹表示,「《魷魚游戲》第一季與觀眾見面花了12年,但它只用了12天就成為最熱門的Netflix劇集。」
「從一個制片人有那個創意和想法,到觀眾看到作品播出的那一刻,可能已經過去三四年了,這還是好的情況,因為這個想法和創意能夠被甲方看到,并有機會拍出來,就已經是幸運中的幸運,但這個過程很漫長,也很繁瑣。」

《魷魚游戲》官方海報「圖源 豆瓣」
尤丹提到,「制片人也只是一份工作罷了,其實就是一個上班族,一個普通的打工人,為了做出更好作品的普通人。」對于選演員這個事,一般還是會尊重導演,尊重公司和平臺,匯集大家的想法,各抒己見,同時參照演員的檔期和配適度。最終選擇對項目最合適的主創。」
在選演員這件事上,光汐也曾經一度遭遇了挫折。
當時他還在做自己的第一個項目。一切都準備周全之后,平臺突然決定強塞一個女一號進來。他在美術進組一周之前停掉了這個項目,也跟平臺鬧得特別僵。因為他覺得,這個行業需要出現一些新的陽光、新的畫冊,如果平臺這么任性的話,那還不如不做。
盡管如此,光汐和尤丹還是堅守著自己的崗位職責,在影視制作的路上不斷地探索與成長。
剛成為制片人的時候,尤丹總是想著要做一部什么樣的作品,才能想讓更多的人看到以及產生共情。但是后來她明白,影視劇就是一個審美生活日常化的產物,是大眾文化的記錄者,作品即人,你拍什么題材,講什么故事,傳達什么價值觀,都影響著年輕觀眾。你的審美,你的三觀決定了你會做出什么樣的作品,機遇與挑戰總是并存。
光汐也表示,短劇、短視頻代替不了長劇的點在于,長劇能給人力量。「它的力量不是快捷式地打一個叉,而是那種能滌蕩在人的心里的東西,就像一個人合上一本書的時候,會感覺自己變得空靈了」。
在作品之外,「如何做好一個制片人」也是光汐和尤丹共同關注的話題。
在談到「平臺制片是不是進入制片人行業的一塊很好的墊腳石」時,光汐很認同一位前輩的一句話:如果一個制片人都沒有去劇組干過最累的活,沒做過采購,也沒買過一顆釘子,就沒法去做預算,也不能稱自己是個制片人。
在面對「如何處理自己與劇組其他工作人員之間關系」這個問題的時候,光汐表示,「我覺得劇組里的很多人都不容易,都是拋家舍業來的,為了賺口辛苦錢,幾個月都不著家。就算你不能把所有人都當作有夢想的人,但是你起碼要把他們當人看。你要考慮到他們是否吃的好,住的暖,是否能用心去工作,如果你作為一個制片團隊,都沒有把這些人當人看,就一定不是一個好的制片團隊。」
尤丹也提到了類似的觀點,她愿意體諒劇組工作人員的辛勞,但同時也要一起帶著解決方案。她表示,「在工作中,請務必珍惜自己與他人寶貴的時間。我的工作態度是今日事今日畢,就算做得不完美,也要每天把該做的做完。劇組伙伴們的工作周期大都持續很久,大家一起工作一百多天,在工作中可能會遇到各種問題,也需要情緒的疏解,一定要有一個人是能夠讓大家想起來就覺得安心的,我希望自己可以成為一個讓別人一想到就感到很安心和篤定的人」。
「春天」只偏愛有準備的人
「冬天來了,春天還會遠嗎?」
這個問題的答案尚未可知,但可以預見的是,等待「春天」的過程也許會很困難,也許會很漫長。
光汐說,很多人覺得有的劇很好拍,因為場景切換并不多。但實際上,拍攝過程中物料的調配和使用流程都非常復雜,而且很多拍攝相關的技術性問題也很難處理。
尤丹也表示,制片人是一個要能接受持續辛苦,要能熬得住的工作,因為制片人永遠在從頭開始。她認為,「一部作品結束,它就像一枚時間膠囊一樣,你的那一段創作生涯就永遠被埋在那個片場了。你永遠是處在一個不斷超越自己的過程中,今天的你要比昨天的你懂的更多、知道的更多,更了解觀眾、市場和平臺,然后你才有可能去做你的下一部作品。」
但一個人的時間和精力總是有限的,甚至一代人的視角和觀點也可能是局限的。光汐認為,很多傳統的影視公司之所以感覺乏力,正是因為他們沒有一套很清晰的培養下一代的體系,最好的解決辦法是扶持新的一代人去抓住他們更了解年輕人的東西。

光汐希望能夠有新鮮血液注入到影視行業,但是他發現,現在很多想進入這個行業的人其實并不知道制片人到底是一個什么樣的存在。他在采訪中強調,不要不知道的時候就去做選擇。
他說,「干這個行業,首先第一點非常重要的就是天賦和熱愛,熱愛才是讓人能堅持走下去的很重要的一個東西。其次是審美,因為策劃本質上并不是我在某一個方向非常專業或者怎么樣,而是我有一個統籌策劃的能力,以及挖掘人才的能力。」
對此,尤丹也表達了她的觀點,「在成為制片人之前,你要清楚在整個影視生產創作的鏈條上,自己有什么極致長板。這個長板可能在創作,可能在制作,可能在于對社會的洞察和選題能力,首先你要認識你自己,了解自己是否擁有極致的長板,如果有的話,就發揮這個長板,讓自己更加符合職業訴求,找機會去做自己的作品。」
「畢竟,制片人最大的困難是開發作品過程中的不確定性,因為都是單片致勝的,但孵化一個項目是漫長的過程,幾年不等,青春中沒幾個幾年,有可能孵化到某一階段,項目就做不下去了,也有可能因為你的專業和外部條件的天時地利人和,讓項目又有轉機或有新的可能。所以要耐得住寂寞,以及有一顆強大的心臟。所以,怕什么真理無窮,進一寸有一寸的歡喜。」

尤丹在劇組片場「圖源 受訪者」
尤丹回憶曾經有過一次采訪香港知名女性制片人施南生的經歷,當時她問對方說,能不能回憶一下你自己職業生涯里的閃光時刻。施南生的回答讓她很意外,直到現在尤丹回憶起那句話的時候,都會覺得很敬佩。
「我好像從來都沒有刻意回憶過,我感覺我每天都在低頭干活,一干就干到今天了。」
現在尤丹回望自己的職業生涯,她總是在準備和期待自己的下一部作品,希望下一次的自己可以做得更好。
作為制片人,尤丹最大的動力就是希望去表達大部分普通青年們關心的故事。例如好的愛情劇,可以影響和改善當代青年的愛情觀;好的職場劇,可以推動青少年對于一份職業的規劃。她希望那些感動她的故事,也可以去感動更多人,影響更多的人。她說,「把你喜歡的故事去講給想聽的人聽,我覺得這是制片人這個職業讓人痛并快樂著的原因。」
而對于光汐來說,他目前最大的動力是想和自己目前的創業伙伴們一起把自己的公司做好,這也是他選擇離開上一家公司的重要原因。他要讓夢想的種子重新發芽。
1號結語
很多時候激勵光汐和尤丹走下去的,是那些于市場沉浮之中悄然面世的優秀作品。
光汐很少會碰到那種想要奉之為神的作品,但他也常常會因為看到了好的作品而感到興奮。譬如《覺醒年代》,光汐看這部劇的時候熱淚盈眶,又覺得阿鯤作的曲特別好,特地給阿鯤發微信說,「我太喜歡你這幾年來做的事了」。

年初春節,尤丹和父母一起看了《人世間》。90后的她之前很少看這類作品,但真正看到這部劇的時,她被觸動了。「劇里人性至善的光輝,凈化了多少觀眾的靈魂。太多地方讓我淚流滿面。人生苦短,平凡的我們,撐起屋檐下的煙火。或許除了生老病死,其他都是擦傷。」
當時就想著,「有生之年,我在什么年紀可以做出這樣一部作品?就是那種讓觀眾能凈化靈魂,發現人性光輝,看完之后覺得自己也要做一個善良的人的作品。」
后來她還給行業伙伴,《人世間》的制片人之一龐建發了微信,說「這部劇讓我回憶起太多,甚至感受到自己真的老了。感謝你們這部劇,讓我明白人要記得在苦難的日子里熠熠生輝,也要記得在顛沛的日子里堅持不懈。」

尤丹感受到,越是在整個行業處于相對迷茫狀態時,越有這樣高度的精品面世并進入市場,這就說明這個行業是真的有一些人在很努力地想要進步,想要創新,想要探索,想要推動,很努力地想要做出好的作品。匠心就是做好一件事情,初心就是一直做好一件事情。
而這,也是光汐和尤丹共同的理想與追求。
尤丹的身上還保有新聞人求真務實的品質,光汐的身上不變的是逐夢路上的赤子之心。盡管他們也曾感到挫敗和迷茫,但在認清了制片人這個職業,認識了自己之后,他們依然選擇熱愛它,并為之奮斗。
注:文中光汐為化名。






